国内视野
威廉·伊斯特利:不同形式的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来源:腾讯网 作者:发布时间:2016-08-24
两种不同的腐败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种是分散化腐败,另一种是集中化腐败。
在分散化腐败情况下,有很多腐败者进行掠夺,而且他们之间并无一个协商机制。而在集中化腐败情况下,一个政府领袖组织了全社会的所有腐败活动,决定每一个官员在腐败活动中应得的份额。
分散化腐败类似于在旅行过程中遇到的多个路障,比如说,在扎伊尔,你在每一个路障处遇到的士兵都是一个独立的掠夺者,他们并不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其他掠夺者的影响。旅游者的财富是每一个掠夺者都想获取的公共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品悲剧发生了。每一个士兵都想获取尽可能多的贿赂,因此,在分散化腐败的情况下,“掠夺率”就要高于集中化腐败。实际上,在分散化腐败的情况下,“掠夺率”可能非常高,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贿赂总额要低于在一个较低的“掠夺率”情况下的贿赂总额。随着“掠夺率”的提高,旅游者会更倾向于寻找机会避免被敲诈勒索。他们会走那些有较少路障的路线,携带更少的财物。分散化腐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向激励最坏。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导致分散化腐败的破坏作用更强。一个人因受贿行为而被惩罚的概率与政府的实施力度正相关,与腐败官员的数目负相关。在分散化腐败的情况下,政府非常弱,许多官员都存在腐败行为。即便政府抓获了一些腐败官员,某一官员被抓的几率也很低,因为腐败官员的数目很多。因此,腐败现象存在着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分散化腐败的程度比较低,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很有可能被抓获,因此官员就很少会去从事腐败行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当分散化腐败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每一个官员被抓获的可能性很低,因此腐败程度就很高,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集中化腐败的情况下,一个领导者会寻求最大化腐败集团的所得。这个领导者会对被掠夺者相对“仁慈”,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掠夺太多的话,受害者会采取逃避行为,自己所获得的总贿赂也将减少。因此,集中化腐败集团的领导者,如印尼的苏哈托,会在各个受贿环节设置比较低的“掠夺率”,争取最大化整体的受贿所得。在集中化腐败的情况下,在每一层级,对掠夺规模都有一个监督。任何想掠夺比领导者规定的数目更多的官员将受到惩罚。
由于这一监督机制,恶性循环便不会发生。相对于分散化腐败,集中化腐败的破坏程度较低。
更一般地,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会选择一个对经济增长不至于造成太大伤害的腐败水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掠夺所得依赖于经济规模。一个存在分散化腐败的弱政府则没有这一维持经济增长的激励。每一个掠夺者的力量都很小,不足以影响整体经济,因此他就会尽力去掠夺受害者。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腐败对印度尼西亚造成的恶劣影响要弱于扎伊尔。在扎伊尔,政府很弱,存在很多独立的腐败官僚;而在苏哈托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力量很强,可以从上到下制定一个腐败“纪律”。扎伊尔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为负,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至少到最近如此)。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腐败的类型同样发生了一些变化。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前就存在一些腐败,但在中央的集权统治下,腐败行为是自上而下的集中化腐败。但在经济转轨之后,产生了许多独立的力量中心,形成了分散化腐败。这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的腐败程度要高于转轨前。
(作者:威廉•伊斯特利;本文选自《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
作者简介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于198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2001年在世界银行工作;2001-2003年任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和国际经济学研究所(Institution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高级研究员。伊斯特利的研究领域包括非洲、经济发展和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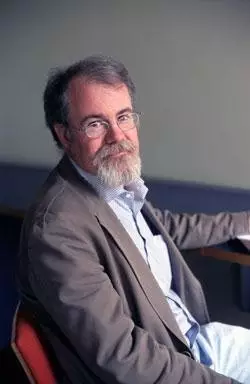
图书简介
本书作者根据他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剖析了自二战结束以后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推行其政策建议的成败案例,破解了经济增长之谜,揭示出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有经济主体,不管是普罗大众、企业、政府官员还是援助机构,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成功的经济政策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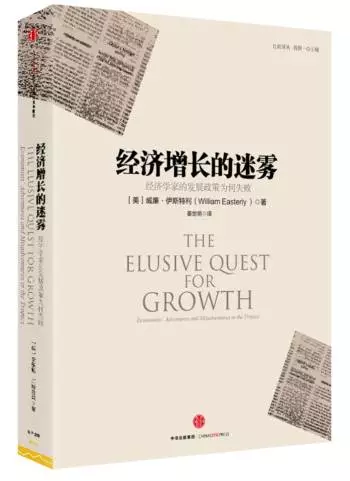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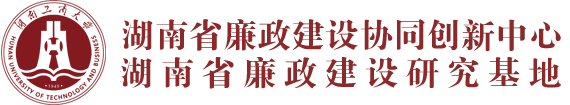

 国内视野
国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