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聚焦
德国反腐刑法的国际化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韩毅发布时间:2017-06-29
腐败是人类的公敌,而刑法是防治它的重要手段。德国的反腐刑法既有根植于国情的深厚传统,又与国际接轨,不断实现自身的更新与完善。
德国传统与国际发展
不同的民族依其历史和国情,对腐败各有不同的理解。现代德国不再奉神权和采邑为基础,转而以军队和吏治为支柱。相对于决策的“官”,“吏”指的是执行者。他们通过专业考核获得资质,不受各届政府的影响,敬业求实、强干精进,成了知识与能力、荣誉与权威的化身。即便是“清算普鲁士”的魏玛宪法,也在第129、130条继受了吏治传统。马克斯·韦伯更强调行政要恪守客观中立的定位,低效、混乱便失去存续意义。在这一背景下,1871年的《帝国刑法典》主要规定了行政腐败这一种样态:公务员在职务范围内收受、索取或应允各种礼物或其他惠利,则依其为此实施的行为是否违背自身义务,分别处以300马克以下罚金或半年以下监禁,或以受贿罪处5年以下劳改。军警与司法腐败以此为基准,因为他们当时和教师一样,都属于特殊领域的公职人员。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德国的“腐败”不仅包括“受贿”,即收受惠利实施违背义务的行为,而且包括“受惠”,即为正常实施公职行为而“不当得利”。
该规定直到1997年都未经历实质性变更,因为它能够满足德国内部的实务必需。但国际规定最终还是引致它的改革,而这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经合组织”于该年出台一部打击外国官员在国际商务关系中受贿与腐败的公约;第二,同年欧盟拟定了一部打击欧盟官吏与公职人员腐败的公约;第三,欧洲议会也于同期通过了一部横跨民刑的反腐公约;第四,联合国于2003年颁布了反腐公约,至今仍是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尽管它们规制的情形与自己并无关联,但作为成员,德国却有义务通过立法形式将其“内化”。
犯罪主体
首先,在迄今的基本行为构成要件(第331、332条)之余,如今重设的第333、334条也追究施惠者或行贿方,第335条则规定了行贿受贿的加重情节。其次,新增的第108b、108e两条追究贿选行为与议员腐败。最后,第299条还规定了商务交易中的腐败,其下的第299a、299b两条专题处理医药领域中的行贿受贿。比起原来只有本国的公务员才能受到追究,现在的犯罪主体一则扩展到外国与欧盟的一切公职人员,包括各级官吏、司法(含各种非诉程序)人员与议会成员,二则国内外各级议员的受惠与受贿也会成为追究对象,三则私人与公司的腐败以后都会获罪。
这番大幅扩张会在实践中引发怎样的震荡,或可通过一个案例以管窥豹。西门子等德国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但在一些国家,它们必须向主管部长发放“红包”,后者才会与之签订合同。按照德意志的传统观念,这种“交易习惯”并非任何不道德的行为,而是根据目标国的具体情况采取的必要对策。鉴于这样能够增加本国出口,有关开销甚至被视为“有益的支出”,从而享受税收蠲免。德国刑法只管保护德国行政的廉洁高效,企业本身并不在调整之列;至于外国部长的所作所为是否妥当,则是其所在各国应当监管的问题,德国法律无权越俎代庖。然而按照新法,无论本国企业还是外国部长,都会成为打击对象。至于这给本国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域外高官的问罪又能否得到执行,则尚需进一步的资料予以证明。
行为类型
与犯罪主体的扩张相适应,新法覆盖的行为也已分成多个类别。
第一,经典的行政腐败如前引条款所示,该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给”与“拿”的客观行为,为此实施或理所应当(受惠)或违法乱纪(受贿)的公职行为,二者之间有对应关系。遇有数额特别巨大(5万欧元以上)、腐败行为持续发生、有组织犯罪等加重情节,今可加重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司法腐败。在“三权分立”的官方意识形态下,德国“公务员”是行政的象征,法官则是司法的化身,二者必须划清界限。于是《刑法典》第331条另辟第2款专门针对法官受惠、第332条第2款配套规定法官受贿。但其结构却与各自的第1款并无二致,也依标的行为是否违背义务,分处5年以下或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欧盟指令和2015年《抗击腐败法》的结果,这里的“法官”要做广义解释,不仅包括欧盟各大法院的成员,也包括外国的法官以及国内和国际的调解员、仲裁员等。
第三,政治腐败。其下又分成传统和新兴的两类:资助政党与选战和议员腐败。首先,按照《政党法》,得票超过5%的各党依其所获选票在这些党派中所占的份额,分取相应的税金作为日常经费来源。遇有选举或其他特殊事由时,若有私法主体(包括法人与自然人)向某政党进行捐赠,后者有义务向联邦或州的议会管理部门申报。否则后者有权收回前述公共财政的拨款,然而此举系财务处分而非刑法性质。其次,《刑法典》1994年新增了一项,起初仅限于议会就某具体事宜进行表决时投赞成、反对抑或弃权票的买卖,其下又分为消极(被人求上门来,第1款)和积极(主动兜售投票,第2款)两种情况。这种局限性系有意为之,因为过于宽泛的行为构成会使反腐刑法成为议会各党政治斗争的工具,最终使立法部门陷于瘫痪。但到2014年,德国还是服从了欧盟的要求,将客观方面扩展到了所有“在履行议席职能过程中受委托或按指令做或不做某事”的行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这里的议员也不限于德国联邦、各州和乡镇的议员,而且也包括“欧洲议会”或国际组织中相当于议会机构的成员。根据2015年的又一项修正案,与上文“外国部长”同理,外国议员也成了本条的管辖对象。
第四,商业腐败。第299条也用两款分别规定了公司的职员或受委托方主动或被动腐败的行为。其下又分两种情况,即在选购货物或服务时以不正当的方式优待国内外竞争中的某一方,或未经公司允许而做或不做某事从而违背义务,借此为自己或第三人索取、应允或收受惠利。但传统的前者本是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对象,而2015年引入的后者也与刑法中既存的“违背忠诚义务”发生竞合,所以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腐败。
于是商业腐败的重点转入了医药行业:许多药厂以各种方式向医生提供激励,使其总为患者指定本厂产品,甚或避免开具竞争对手厂商的药品。鉴于自营诊所的医生既非公职人员,也非法定抑或私营保险公司的员工,最新的法律都拿他们束手无策。于是2016年,德国专门新增了299a、299b两个条款。今后医生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索要、应允或收受“没有正当来源”的惠利,则无论其所开具的处方在医学上是否正确,医药双方均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处以罚金。
刑法并非打击腐败的唯一方式,根本上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制定行为守则,先行内部监控。如果这一切都未能遏止腐败的发生,德国法的规定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怎样一方面立足于具体国情,设置必需的行为要件,另一方面跟随时代与技术的进步,与国际发展潮流接轨。这也有助于加强和丰富国际合作,追缴流至境外的赃款,最终让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回到原处。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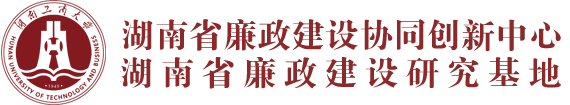

 国际聚焦
国际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