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视野
腐败的文化透视——理论假说及对中国问题的探析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胡伟发布时间:2018-07-03
文化因素论和现代化因素论通常是国际学术界有关腐败发生学的两种主要理论假说。腐败的发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在某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腐败现象显然比另一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更普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或“腐败的民俗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腐败的发生是现代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叠加结果,其中文化因素尤其不可忽视,既有一般性的腐败发生的文化诱因,也有特殊主义的“二元文化结构”的作用,其后果是形成了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腐败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文化的建设对于中国的反腐败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意义。
腐败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对于不同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特定的历史传统与国民性、社会与政治体制的类型、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取向以及反腐败的力度和政策选择等因素,都对腐败的消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国际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来看,现代化因素论和文化因素论通常是对腐败现象高发进行解释的两种主要理论假说。本文旨在从文化的角度对腐败现象进行解读,重点剖析改革开放后中国腐败发生的深层原因。本文试图说明,腐败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并已成为社会的流行病,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深处,形成了后果极为严重的“腐败文化”。因此,中国的反腐倡廉在强化治标手段的同时,还要注重廉政文化的建设,实行民主和法治,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入手根治腐败。
一、腐败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现象?
腐败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每个社会都难免有腐败问题的存在。但在某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腐败现象显然比另一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更普遍。这说明腐败的发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国际上研究腐败问题的著名专家S.R.艾克曼曾指出:在文化的层面上,腐败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意义。“一个人拿来行贿的东西,在别的社会可能只被看作一件礼物。一位政治领袖或政府官员帮助朋友、家人和支持者,在某些社会受到人们的赞扬,在其他社会则可能会被视为腐败。”①腐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存在更多的腐败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国家民众关于腐败的观念模糊,腐败被视为正常行为甚至是“文明”的行为,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美国著名发展社会学家胡格韦尔特指出:贪污受贿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和发达国家相比要广泛得多、更多地涉及每日生活方式,它造成的经济生活混乱的程度比在发达国家中要大很多。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贪污受贿席卷生活的一切领域,触及所有的人,正像一本描写西非的书中所说,“总的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能被买走、能被敲诈走的东西没有被敲诈走”。另一本讲述第三世界的书则说:“在公众要与官员打交道的一切场合,行贿受贿现象都不露痕迹地存在着,就连法律也靠支付能力执行”。“行贿受贿现象就像木材中大量存在的白蚁一样充斥公共生活的每一部分……无时无事不行贿受贿,甚至太平间的管理员把尸体交给死者亲属也要敲一笔竹杠”。③在这些国家,腐败已成为了社会流行病,是政治肌体的恶性肿瘤。
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腐败行为被视为正常,至少是习以为常,很少受到文化上的敌视。美国学者大卫·贝里指出,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中,腐败分子并不受其社会的责难,“实际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是遵从其同辈、家族和朋友强有力支持和称赞的行为。例如在非洲和印度,一个人利用其职权为其亲友谋取职位并不被看作是违背道德的。”④一个德里的商人甚至说:“贿赂与腐败对我来说全是舶来货。它们蕴含的观念也是外国的东西,我想在印度,人们不知道这两个怪词。向政府官员送礼是必不可少的礼节和经营企业的高雅文明之道。”⑤这正像瑞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在研究了亚洲一些国家的腐败问题后所指出的,这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腐败盛行,以致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民俗学”,“这种民俗学对于人民怎样处理私生活,他们怎样看待政府旨在巩固国家、指导及促进发展所作的努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容易使人们认为,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当忠于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⑥在缪尔达尔看来,腐败在这些国家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上述观点即为腐败的泛滥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解释,即在某些社会中,存在一种“腐败文化”,即把贪污受贿视为正常,腐败成为社会规范可以接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这是政治文化极为愚昧和落后的表现,按照现代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实际上是官员道德和公民道德都十分败坏,是非不清,黑白颠倒。印度的黑钱调查委员会曾哀叹存在着“越来越重视物质价值的趋势和以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迅速致富的风气”。正如加纳政府负责调查行贿和腐败的委员会在1975年的一份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广泛存在的行贿受贿现象,形成道德败坏的空气,是对政府的莫大讽刺。⑦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一个人要想出污泥而不染就十分困难,以致腐败现象大行其道,广泛流行。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则把腐败的大量滋生看作是现代化的产物,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腐败发生的诱因也会增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腐败的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⑧他认为,英国18世纪和美国19世纪的腐败高峰期,恰好是与这两个国家受工业革命的冲击和新的财富源泉的开发的时期相重叠,这不是偶然的。这意味着,腐败不仅可能是某种文化的产物,而且也通常是现代化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副产品。正像亨廷顿所说:“某些文化中的腐败现象可能比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更为流行,但在现代化处在最轰轰烈烈的阶段时,大多数文化中的腐败现象似乎也最为泛滥。”⑨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文化因素论和现代化因素论通常是国际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腐败高发原因进行剖析的两种主要理论假说。这两种假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把这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进行分析。当然,对于不同时空的社会来说,这两种因素的重要性不是等量齐观的,因果关系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不妨说,腐败或多或少与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但腐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则要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二、中国改革开放后腐败现象发生的文化成因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积极的意义已经和正在被人们所认识。同时,一些消极现象也沉渣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腐败现象的不断恶化。对于这一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固然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分析,但文化因素和现代化因素无疑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两个主要原因,而且可以把两者叠加在一起进行分析。
一方面,从现代化的因素来看,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也不是没有启动现代化的进程,但那时的社会资源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当时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形式和政府对经济运行的集中统一管理,加之强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群众运动式的反官僚主义和反腐败的抑制,腐败现象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新的财富源泉、新的权力结构、新的生活方式,这使得腐败的形式也错综复杂,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如有政府官员接受下属单位信用卡的,有用公款去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或者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的,这些形式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社会处在转型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解体,而市场经济秩序又未形成,新旧体制转换尚未完成,制度缺陷比较明显,给腐败以可乘之机,所以腐败的发生率较之改革开放前高出了很多。⑩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腐败现象滋生泛滥的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这些因素与现代化因素发生“共振”,对腐败的高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腐败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的流行病,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深处,其原因也必须从社会文化的深处去寻找。对此,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中国的腐败现象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缺少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无论是在官吏还是民众中都存在着极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倾向,诸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就是真实的写照。在毛泽东时代,革命后的强大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曾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传统的腐败文化进行了抑制。而改革开放后,这些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在宽松的氛围下得以强烈反弹和猛烈释放,甚至变本加厉,革命后的意识形态日薄西山,新的主流价值体系又未生成,整个社会缺乏伦理道德的支撑,是非观念发生扭曲,“一切向钱看”成为了实际的社会法则和价值标准。其后果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主要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在社会政治领域主要就是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因此,腐败现象只是传统文化劣根性恶性膨胀的一种必然反映,而且随着这种文化上的堕落,腐败现象也呈现普遍化和社会化,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不仅政府官员腐败会导致政治腐败,而且非政府结构和一般民众之中的腐败之风也愈演愈烈,腐败已经由政治层面向社会和文化层面渗透,且彼此互相助长。
第二,改革开放使社会的价值观不断发生变化,对于某些社会行为的评价失去了普遍公认的准则,因此对不少腐败现象的界定和甄别也就不那么明晰了。例如,贪污贿赂属于腐败一般是没有争议的,而请客送礼是否属于腐败则就很难一概而论了,至于公款吃喝、旅游,即使从规范上被认定为腐败,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多也会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工作的必须或人之常情,实际上通常并没有被当作是腐败来看待并加以处理。同时,由于对是非曲直的判断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变化,有些行为在过去被看作是腐败,在现在可能就被视为正常和正当。例如,政府部门和官员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而从事的某些经济行为,在改革开放前会被认为是以权谋私和腐败,而改革开放后则一度被视为正常甚至加以提倡,干部“下海”就是一个例子;过去被称为是“投机倒把”的某些行为,现在却恰恰被当作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手段。对于这类问题,有些的确是合理的,是社会出现的新生事物。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进行反腐败,也必须把腐败现象置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加以透视,不能用老眼光老观念来看待新问题,把一些符合社会发展的新事物视为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变动不居确实也使反腐败陷入了文化观念上的困境,使很多腐败行为得以披着改革开放和新生事物的外衣蒙混过关,甚至鱼目混珠。
第三,改革开放后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种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即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从主观方面看,不少人包括一些党政官员把反腐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害怕反腐败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认为如果廉政搞得太好了生意就做不成了,所谓“四菜一汤,生意跑光”,就是一种反映。从客观方面看,现实生活中确实也存在一些所谓的“两搞干部”,即“一手搞发展,一手搞腐败”,有一些腐败官员在任期间“政绩”不凡,一些经济搞得比较活的地方往往腐败现象也错综复杂。于是,不少地方和部门奉行的是“先发展经济后反腐败”的逻辑,甚至提出“经济要上,廉政要让”。问题是,腐败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吗?实际上,利用腐败发展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短视行为”。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研究,除了个别的情况外,在发展中国家腐败的成本通常超过其效益。(11)国际上对腐败的成本-效益分析的一般结论都是腐败的“成本”大于其“效益”,利用腐败的手段发展经济和推动现代化最终是得不偿失,中国也自不例外。但中国社会缺乏对腐败的这种理性认识,诸如“经济要上,廉政要让”之类的模糊观念仍很普遍,这不可避免地干扰了反腐败的正常开展,尽管反腐败也受一些客观原因——如利益上的、体制上的原因——的制约。
由于以上三方面文化观念和认识上的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腐败的判定总的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特点,给反腐败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同时也助长了腐败之风。对此,可以借用“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的概念加以具体分析。按照美国学者阿诺德·海登黑默的分类,腐败可以从人们的认识态度上区分为“黑色”、“灰色”和“白色”三类。所谓“黑色腐败”是指受社会普遍谴责的腐败行为;“灰色腐败”则是有广泛争议的腐败行为;而“白色腐败”是社会大多数人不认为应当受到惩罚的腐败行为。(12)改革开放后,我国腐败现象总的来说是从黑色向灰色和白色转变,有关腐败的标准模糊不清,人们对腐败现象也趋向麻木不仁,甚至出现了“笑贫不笑贪”的灵魂扭曲现象。需要说明的是,存在腐败现象并不可怕,只要一个社会有良知,腐败并不难克服和抑制;真正可怕的是一个社会丧失了对腐败的判断力和批判力,从而形成“腐败文化”并使整个社会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腐败文化的深层次分析:特殊主义下的二元文化结构
虽然民众对腐败现象总体来说越来越麻木不仁,腐败之风也愈演愈烈,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我国民众对腐败现象完全不痛恨了。实际上不少民意测验和调查数据都反映出人们对腐败和社会风气不正的担忧和不满。根据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年联合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关注焦点与未来预测调查所显示的结果,在所有18个选项中最令人不满意的是“社会风气”(包括腐败之风),占被调查者的82.2%。问题是既然民众有那么高的觉悟,腐败之风为什么还愈演愈烈呢?如何解释民众的这种“高觉悟意识”与腐败的实际发生率居高不下的事实呢?制度缺陷及由此造成的民意不能对腐败进行有效制约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从文化态度上分析,也不能过高估计民众的这种“高觉悟意识”。
实际上,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对腐败既深恶痛绝又身体力行。当腐败涉及到他人而自己没有得到好处时,就表现得义愤填膺;而一旦关系到自身的利益,则另当别论。如果说某个人没有与腐败同流合污的话,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富有正义感,而是他没有掌握相应的资源。一个在台下对腐败口诛笔伐的人,一旦上了台很可能也就成为了腐败分子。甚至在台上的人一方面对腐败大加鞭挞,另一方面暗地里又大肆贪污受贿,形成了所谓的“两套话语系统”、“两套游戏规则”和“两面人”现象。这种“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副产品,即著名作家柏杨所说的“只我例外”的心态:“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约束。”(13)因此,对于不少人来说,反腐败或对腐败的义愤只是对他人而言的,自己则可以例外。
从上述意义上说,虽然人们对腐败也有不少模糊观念和认识误区,“灰色腐败”甚至“白色腐败”的数量越来越多,但仍不能一般地说中国是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缺乏腐败的概念和标准,不知行贿受贿是腐败,而实际上大多是明知故犯。因此严格地说,中国在社会文化上所缺乏的是有关腐败的“普遍性”标准,因为人们对腐败的标准通常都是“特殊性”的,因人而异的,只我例外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在理论上缺乏对腐败进行判断的普遍性标准,实际上主流文化(官方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认定了腐败在法律或者是道德上的普遍性标准(除了一时还难以确定的“灰色”方面),但这并没有转化为民众的普遍性标准,大众文化仍带有很大的传统色彩。例如,请客送礼是主流文化所批判的,但在大众文化中却是人之常情,不请客送礼者反而在社会上很难立足,很少有人会把请客送礼与腐败联系起来,特别是当问题与自己有关时。
这种大众文化心态中的“特殊主义”,使得当前中国在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就造成了一种“二元文化结构”——主流意识形态所宣传、倡导和描述的东西,与社会的实际观念、价值和意识大相径庭,理论与实际脱节严重,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当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抱着“独我例外”的心态来对待主流价值标准时,主流价值就被扭曲和消解了,致使社会“潜规则”盛行。所以,在腐败问题上的模糊概念和认识误区只是腐败之风得以助长的一个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特殊主义”文化对主流文化普遍性的消解,使腐败文化得以生成和盛行。
四、从腐败文化的后果看廉政文化建设:意义与途径
当腐败成为了一种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参与腐败就不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果不使用一些请客送礼甚至行贿的手段,很多事都办不成;而对于有个一官半职的人,如果不加入到腐败者的行列中,就很难生存下去,特别是那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很难逃脱腐败文化布下的天罗地网。从《中国青年报》所发表的时论《实权人物小心陷阱》中,对此可略见一斑。作者说:“我曾听到一个‘成功人士’谈如何‘搞定’一些官员:只要是人,他就有弱点,他就有喜怒哀乐,投其所好,没有摆不平的。要么他爱财;要么他贪色;要么他还想继续升官;要么他怕老婆;要么他家中有病人;要么他的孩子不成器……如果所有这些他都不必面对,他还有上级、同僚、同学、战友、朋友的面子、关系需要照顾,拉住他周围的这些人,也能让他就范。实在不行,还可以来硬的,把他的上级拉下水,把他必须打交道的部门拉下水,让他们制约他,说服他……”(14)
在这种腐败的文化尤其是腐败的官文化下,即使有个别清正廉洁者,在腐败氛围的压力下,往往也不得不同流合污。如果真的想洁身自好,则可能受到孤立、排斥、打击,甚至被调离工作岗位。(15)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好人”被“坏人”拉下水,“好人”越来越少,“坏人”越来越多,以致最后一个地方或部门所有的人都腐败的官文化所腐蚀。近来屡屡发生的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班子在反腐败中被“一锅端”的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这并不是为腐败的官员推卸其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在这种腐败的官文化当中,一个人要“出污泥而不染”,不仅需要觉悟和良知,而且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毅力。这正是为什么虽然中国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腐败之风仍难以刹住甚至是愈演愈烈的深层次文化诱因。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反腐败的斗争的艰难之处是在于缺少一种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围,没有一种良好的文化形态来激浊扬清,敦风化俗。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加强廉政文化的建设,在全社会树立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这就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普及法制观念,建立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香港在70年代的“廉政风暴”中,除了惩治和防止腐败行为,还注重开展“价值革命”,以提高公众对腐败的认识、对政府的信任及伦理道德标准。廉政公署不仅通过访谈和大众传媒来进行宣传教育,而且还把反腐倡廉的内容溶人中小学的正式课程中。(16)中国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并达到治本的目的,也必须进行政治文化的革命,树立一种反腐倡廉的公民文化,使腐败现象为人民所不齿,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正气压倒邪气,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源泉。因此,中国当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廉政文化的建设,不是单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这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需要加强新闻和舆论的监督,需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这是因为,中国的腐败文化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但源头是在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中国具有悠久的“官本位”文化,政府官员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如果这些官员的权力不受约束,腐化堕落,就必然会上行下效,最后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病。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廉政文化的建设需要从掌权者入手,而首先是要对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英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成为越来越多人共识的至理名言。无论何种社会,以权力制约权力都不失为在制度层面上克服腐败的一种根本方法,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它虽发轫于西方社会,但不应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历史不可谓不注重从文化和思想意识上解决腐败的问题,但关键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例如,历代统治者都大力倡导儒家的正心、修身的“内圣外王”之道,专制王朝也企图依靠“君君臣臣”的道统来培养对皇帝效忠的“清官”。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虽然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员的行为,却无法防止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每一封建王朝的倾覆,无不是最终由于政治腐败猖獗不治所致。究其原因,就是缺少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不能从根本制度上解决对权力的制约问题。
当前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进行思想领域的教育是必要的,如号召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头廉洁自律,以及利用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件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等等。但单靠这些是不够的,而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形成一套严密的权力制约的机制。这就需要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毛泽东在1945年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治乱盛衰的周期律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来防止腐败的思想。只是他没有着重从制度化的层面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而是诉诸于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结果产生了不少副作用。实践证明,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应当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通过权力制约的机制来实现,包括民主选举、权力监督、舆论自由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文化的建设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只有惩戒警示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民主法治相结合,中国的反腐败才能最终取得成功。而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精髓,也只能寓于现代民主和法治的精神之中。离开了这一点,廉政文化建设就丧失了根本,也不可能取得长效。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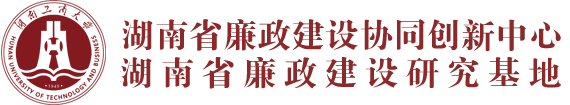

 国内视野
国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