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武陵山区农村“微腐败”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在一手抓精准脱贫的同时,一手抓防治微腐败,才能全面提升广大农民的满意度。武陵山区位于华中腹地,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该片区的农村微腐败问题,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广大农村微腐败问题的一个缩影。
一、 当前武陵山区农村微腐败的特点
武陵山区涵盖重庆、湖南、湖北、贵州四省市。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及四省市纪委网站公布的资料,2017年四省市共通报187起微腐败案件,在农村中发生的有138起。 案件有四个特点。
一是关于扶贫问题的案件多。四省市187起案件中,涉及扶贫问题69起,占37%,远高于其它问题。贪腐类型以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扶贫资金为多。在调研中发现,在扶贫公路等项目实施中,贪腐现象也较为严重。
二是贫困村中涉及扶贫问题的案件比例高。在贫困村中发生的微腐败27起,其中扶贫问题17起,占63%。在非贫困村中发生的微腐败111起,涉及扶贫问题的52起,扶贫案件占总量的46.8%。
三是村支书与村主任涉案最多。涉及村支书的有98起,占案件总数的52%,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案件都有村支书参与。在湖南省,67.5%的微腐败案件牵涉到村支书。涉及村主任的59起,排在第二位。重庆市村主任的涉案率最高,占47%。
四是村干部联合贪腐现象突出。在村寨中发生的138起微腐败案件中,串通起来腐败的有63起。其中,村干部联合贪腐的有50起,占村寨腐败案件的36.2%。重庆、湖南、湖北、贵州村干部联合贪腐占村寨腐败案件的比例分别为43.3%,42%,41.7%,11.1%。重庆发生贪腐案9个贫困村中,4个是村干部联合贪腐。湖北的5个贫困村中,发生2起村干部联合贪腐案。
二、武陵山区农村微腐败的直接原因
通过对武陵山区县、乡、村干部及村民的深度访谈,发现武陵山区干群谈论较多的、导致微腐败的直接原因有5个方面。
有钱就是有能力的观念。农村中先富起来的人,不仅受到村民的拥护,也得到乡镇的关照。在村干部竞选中,一些有钱的候选人通过送礼的方法来拉票,当选的机会更多。在工作上,有钱的村干部说话更能服众。这种观念诱使村干部想方设法挣钱,有些人就铤而走险走向腐败。
宗族化家族化的党员干部圈子。在武陵山片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在较封闭的山区,少数姓氏支配村寨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村委直选过程中,出现了操弄宗族家族关系获取选票的现象。为了把控村支部,个别支部书记甚至只发展三亲六戚入党。不少村民在各种选举过程中首选与自己血缘关系和宗族相同的,期望他们当选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圈子形成后,村干部微腐败费力不多,获益不少。优亲厚友,共同贪腐的行为也就不断出现。
扶贫资金快速增加。扶贫资金增多客观上给贪腐创造了机会。2015年以来,扶贫资金不断猛增。2015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补助地方部分460.9亿元, 2017年达到860.9亿元。预算扶贫资金主要投入到中西部地区。武陵山区各省区也投入海量扶贫资金。在贵州,2016年全省共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65.11亿元。在地方财政扶贫资金中,省级财政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2.38亿元,比上年增长77.9%;市(州)级财政安排13.62亿元,比上年增长106%;县(市)级财政安排39.27亿元,比上年增长236%。 在湖南,2016年中央和湖南省共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7.18亿元,较2015年增加25.66亿元,增长81.4%。其中,中央安排32.18亿元,增长37.99%;省级安排25亿元,增长204.88%。2017年中央和省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达到75.97亿元,比2015年增长141%,比2016年增长32.86%。 扶贫资金重点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并且数量大,种类多,投入急。许多村民并不知道上级扶贫新增了哪些项目,自己能得多少钱,给村干部贪腐留下了空间。
两种治理体系衔接的困难。乡镇及以上政权属于国家行政体系,农村则是村民自治体。两种体系规则不同,不易衔接。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联系主要通过村干部。乡镇通常要管理十几个村寨,工作离不开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和主任的配合。国家既要约束村干部的权力,更要维护他的权威。村干部既不属于行政体系的干部,又受到行政体系的倚重,使他容易瓦解对自身的监督。
有效监督的缺失。上级对村干部的监督主要是乡镇纪委在监督,一方面是乡镇纪委人手不足是常态,另一方面许多精准扶贫的资金是由区县部门直接分配到村里的,乡镇纪委的监督时常偏软。农村中已设立了村纪检委员,理财小组,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同级监督机构,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素质不高,不敢、不会监督,或者与村“两委”交叉任职,形成同体监督。委员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缺乏独立性。村民既不愿监督,同时实施监督难度也大。农村是熟人社会,举报村干部面临长期被报复的风险。只要不涉及自身利益,村民也不愿告发。村民没有查看账目等证据的条件,举报只能靠猜测。
现有的监督体制总体上是不完善的,尤其当村干部联合腐败时,监督制度缺失就更明显。
三、农村微腐败与现代化进程相关联
作为后发国家,走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腐败问题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生,在农村中表现为常常出现雁过拔毛式的微腐败问题。
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现代化过程首先表现为变得更加富裕的过程,渴望获得更多财富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去魅化的过程,传统社会中善恶有报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利益有更多的理性计算,只帮助自己圈子里的或能带来回报的人。在这一阶段,村官传统的为民作主、造福一方的观念在淡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民主、法冶、公正、信等观念尚未成为行动的守则,软化了对腐败欲望的约束。
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 一些人用权力去换取金钱,与之相对,另一些人则用金钱去换取权力。在武陵山区,农民理性计算当村官的成本和收益。在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岀务工的环境下,村干部的䃼贴普遍不高,引发心理不平衡。一些村干部就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经济利益。当村干部职位是通过花费大量金钱(请上级和村民吃饭,给他们送礼物)获取的,这种将权力变成金钱的欲望就欲加迫切。除村干部自身的因素外,某些从事工程承包的商人,也通过种种途径拉拢村干部,以求获得工程等项目,成为村官微腐败的外部推动力量。
后发国家中,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现代化过程是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公民的权利意识加强,对政府的要求随之增加。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经济技术进步,政府也有能力处理更多的公共事务。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逐渐加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有明显的差距,东部和中西发展严重不平衡部,为了在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城市反哺农村,东部支援中西部成为广泛的诉求。大规模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规划,就是对这种诉求的一个回应。政府的扶贫政策、资金要达到村里,需要借助村级组织来实现。微腐败的机会由此增加了。
有效制度时常处于缺位的状态。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动态过程,由于社会的快速变革,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成为常态。只有当腐败行为引起关注,形成社会共识以后,才会创设新的制度来制约它。制度的不完善是常态,监督常常失灵,破坏了防控腐败的制度环境。因此现代化过程也是容易滋生腐败的过程。武陵山区存在预防微腐败的多种机制,但能有效防范腐败的制度依然缺乏。
四、乡村振兴视角下治理微腐败的策略
十九大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设立了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为了推动农村和城市同时实现现代化,城乡人民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规划。乡村振兴是促成农村同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创举。从乡村振兴的视角看,武陵山区农村微腐败问题是农村治理不完善和乡村文明建设滞后的结果。解决微腐败问题,需要切实做到“治理有效”、促成“乡风文明”。
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对微腐败的刚性约束。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县(区)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对农村工作的检查和督促,重拳治理乡村“微腐败”行为。吸收新乡贤、驻村第一书记参与村庄民主管理,从而充实力量,提高民主管理能力,并支持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强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在提高乡村基层治理质量的过程中,构筑防范微腐败的牢固阵地。
以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形成对微腐败的柔性约束。微腐败的形成有其文化环境。根治腐败亟需通过乡村文化改造、文化重建,营建新时代的文明乡风,塑造“微腐败”零容忍文化,从根源上杜绝微腐败。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明辨是非的主流价值观。二是通过廉政教育、专项学习提高村干部素质,通过法治教育提高村民监督、参与能力。
(本文作者陈金龙,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副教授。朱永梅,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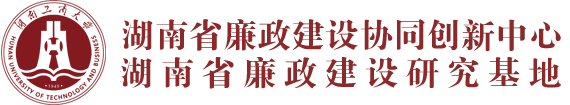

 国内视野
国内视野